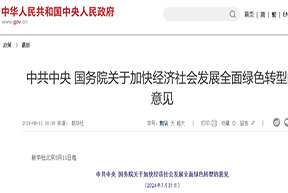倫敦大學學院巴特雷特規劃講座教授吳縛龍以“協同角色的缺失:從資源配置走向城市營銷”為題做報告。
吳縛龍教授從中國城市規劃的源起和傳統開始講起,當今城市規劃師作為一種職業起源于現代國家形成。中國的城市規劃有著強烈的建筑和工程的傳統。規劃師所起的作用受到其所處的政治環境的制約,同時規劃作為上層建筑一部分,也隨著社會的劇變而變遷,規劃在改革開放前后發生了一系列變化。
中國規劃體系實際有三種,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法定城市規劃體系,國土資源部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以及發改委的“五年計劃“和發展綱要。他從政治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對規劃的起源給予解釋:為了解決個體之間的外部不經濟性的交易成本太高,交給第三方規劃;為解決工業化帶來的公共衛生和社會生存危機,需要規劃予以協調。
“三權分治”下的中國城市規劃,到“城”為止,即在國家體制內,不包括廣袤的長期處在小農經濟下的鄉村。中國的規劃體系存在“規劃失控”的問題,根源在于中國的城市規劃是“發展型規劃”,而不是控制性規劃,在計劃體制下的“資源配置”功能,缺少“利益協調“的功能。在市場經濟轉型中,規劃的藍圖角色得到進一步發揮。轉型期城市規劃作用的轉變,從體制分配資源、 單位內部利益,到分配市場資源、公眾利益。
在“企業性城市”的沖擊下,“發展控制”分隔瓦解,規劃都來自地方財政,地方政府成規城市規劃的主體,管理者和投資者。規劃的“地方化(territorialization)”非常明顯。失控的規劃促使發改委系統形成主體功能區規劃,似乎可加強控制的功能。中國的“規劃得益”難以成為福利供給,往往以土地出讓金的金錢形式存在,成為增長機器。“社區”看不到“規劃得益”,對規劃興趣索然。
另一方面,規劃不給發展設置障礙,也沒有成為“增長的敵人”。吳縛龍提到,城市企業化下的城市規劃,增長控制薄弱,土地財政機制下,各級政府都需要分配增長空間,規劃是增長型政府投資的活動,“怎么會自己出錢,綁自己的手腳”。規劃實際上沒有起到控制用地增長,協同發展的作用。
規劃在市場化壓力下也出現變革,向空間規劃方向發展。從關注土地的利用到城市的綜合發展,規劃邊界虛化,力圖體現戰略意圖而不是法定邊界。其實這一現象并不僅出現在中國,英國也是市場變革壓力下興起所謂空間規劃,稱之為fuzzy boundaries。或拋開法定體系,提供不同圖景,例如戰略規劃成為總規的前期鋪墊,或邀請多家單位超越本地規劃。總之,規劃的功能發生重大變化,從資源配置到城市營銷(place promotion),吸引投資、服務于產業落地。規劃從純技術活動成為“規劃事件”,規劃的組織也變得非常復雜。
吳縛龍教授熱為,在國家和區域層面也出現規劃變革,這反映了中央和地方的復雜的博弈關系:一種是中央制定國家發展戰略,選定重點和試點的地區,由地方來執行;另一種是地方自己制造帽子,經過中央認可,體現了中央的權威性。全球經濟危機之后,發帽子的速度顯著加快,因為中國干預經濟的能力加強,必要性加強,擴大資金投放,實行擴大性金融,必然要由中央政府完成,源起在發改委系統,形成空間治理能力。
空間協調性規劃出現在管治尺度上升過程中,再度出現向歸家和區域的上升趨勢,規劃從企業性的工具刀肩負協調職能。例如全國城鎮體系協調規劃,珠三角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等等,試圖重新確立區域發展空間和結構,建立不同級次的管制。但是城鎮體系規劃和跨區域規劃都缺乏協調,例如缺乏明確的行政主體,對資源分配缺乏統籌配置能力,與政策的聯系尚未真正建立。
最后,吳縛龍提到新城和生態城規劃的中國實踐,充分體現了新時期市場轉型下規劃的特點。新城建設和土地開發相結合,成為通過國土地運作促進產業發展的一環。新城開發體現政府和市場結合的模式,規劃上體現了地方營銷打造亮點、吸引投資的特點。中國城市發展擅長打造新城和城市外圍的邊際城市,形成復雜空間關系。新城規劃常常當做龍頭規劃,新城規劃充分體現了市場轉型下的規劃特點,規劃一定要按照合同執行,不再是政府制定任務。招標、項目簽訂、項目評審,都體現市場產品的特點,規劃是一種市場產品,一種政府采購產品,從而新城規劃充分體現了市場和政府相結合的特點。
吳縛龍教授運用國際化的研究視角和范式,對中國規劃的坎坷歷程、恩恩怨怨,提供一個理論解釋的框架。(1)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影響深遠,但未導致國家的退出,政府的管控持續影響經濟的發展。(2)城市規劃在市場化改革中完成了自身的市場轉型,規劃的工具理性使得其順利過渡到以招標和合同為特點的規劃產品的制作,其中涉及各種利益相掛著,起到行政指令不能達到的效果。(3)城市規劃在市場和政府之間找到其特有的位置:由地方政府所投資的城市市場化的政府工具。(4)規劃是政府管控的延伸,這在舊城改造中表現明顯,規劃代表正規的力量,規劃是強調正規化的過程。
如何尋找規劃的“協同的角色”,吳縛龍引用了一些規劃界名人的微博語錄,例如楊寶軍“應當通過強化規劃的管理角色、強調公共利益”,趙燕菁“強調規劃的服務功能,為客戶服務”,仇保興“強調規劃的環境功能,為國家低碳戰略服務”等等。但是吳教授也提出,如何定義公共利益,客戶自身能否協調,生態低碳的倡議為地方捕獲,存在“山寨版”低碳生態城等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后,吳縛龍提出,“后政治”規劃(post-political planning),規劃的制作工程日益產品化,理念去政治化,致力于中性的愿景如可持續發展等。在GDP增長主義帶來的矛盾和危機日益加劇的同時,中國城市規劃或許需要重塑協同的角色,需要規劃超越經濟技術理性,引入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事業,承擔協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