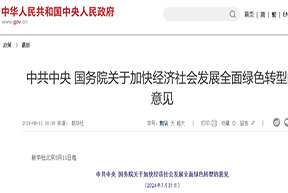導讀
5月21日,“2018第六屆清華同衡學術周”開幕。在上午的“巔峰講壇”上,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尹稚以“新時代的高質量城鎮化”為題,從國家宏觀治理層面,對高質量城鎮化的特征和內涵進行了深入闡述。

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新時代的核心問題是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概括起來就是發展的“不充分”和“不均衡”,這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與之相應的“高質量城鎮化”,目前的討論往往關注諸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技術細節問題。而中國真正實現高質量的新型城鎮化,需要回到對社會核心矛盾的關注和化解。由此,“高質量城鎮化”與國家整體空間治理戰略重新布局,以及空間規劃體系的再造,都有相對密切的關系。
一、重構國土空間治理體系
回顧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進程,通過建立“一體化”的國土空間治理模式,把空間資源進行統一有效的管理是必然選擇。而在具體路徑上,通過立法、規劃和管理之間的相互配合,構建層級清晰、分工明確的國土空間治理體系;通過覆蓋國土全域的空間綜合管理方式,引領國土開發建設,也是大家達成的共識。
中國作為廣域大國,構建統一的國土空間治理體系對解決整體不均衡問題,無疑具有更大的促進作用。但其中有一點需要注意:行政區劃跟真實意義上的經濟區劃和環境區劃有區別。由于我國強行政體制特征,目前遺留了大量經濟區劃和環境區劃不匹配的矛盾。
而從未來發展來看,弱化行政邊界的限制,以真實的經濟區劃和環境區劃為基礎,劃定一系列的特殊政策區域,將行政區劃和經濟環境區劃結合,才能真正推動國土空間治理體系走向區域差異化、動態化和多樣化。
二、區域內部空間治理推動協同發展
1. 自上而下——國家層面差異化政策導向
國家層面應清醒地認識到:區域空間單元屬于不同類型的集群,需要配套差異化的區域策略。均衡不等于空間資源均質化,正如西部大開發絕不意味著在西部可以重建“深圳”與“上海”,它承擔的國土職責與東部地區有本質差異,需要從國家層面進行宏觀調控。
2. 自下而上——多元主體聯動推動區域協調
通過建立政府以外的多主體聯動區域協調機制,解決區域發展中的各類問題。在目前市場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模式下,多樣化、非政府主體的積極參與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基礎。從筆者參與的三輪“長三角區域規劃”研究來看,參與角色的多元化正在逐漸成為非常顯著的特征,也是整個區域規劃具備可實施性的關鍵。這里的多元主體聯動不僅僅是城市之間的協議和聯盟,而是參與地區建設的市場力量形成各種類型的協議、契約與聯盟。
三、大都會地區高密度發展
在自然資源保護和背景條件的制約下,中國真正適于高強度城鎮化的地區非常有限,我們面對的是目前亞洲國家面臨的普遍問題——高密度人居環境下如何實現發展與舒適、發展與保護之間的平衡。
1. 不能以“戰術級”的失誤否定“戰略級”的方向
中國特大城市陸續出現的“大城市病”并不是戰略級的錯誤,很多是空間擴展模式的戰術級錯誤,與政策制定的具體歷史階段有直接關系。比如,深刻影響我國城市規劃領域的雅典憲章,在其五六十年代的高潮過去后才逐步影響中國,而當時主流的發展路徑和發展策略已經遠離雅典憲章,我國當時的發展基礎與憲章發布的年代也已經有巨大的時空差距。
2. 抓住新型城鎮化契機,進行空間結構調整
我國未來一段時間,將在三四十年內完成2~3億人的城市化進程,仍然需要完成大規模的空間建設,這也是中國進行空間結構調整的契機。
首先,需要實現單級集中向多心多核的轉變,既要認識到大都會地區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域聚集作用,同時也要防止單級過度聚集,實現功能和人口在一定地域內的疏解。
其次,通過前瞻性、動態更新的城市圈規劃應對大都會地區的空間治理,為人口和功能疏解及區域協調發展提供科學依據。基于大數據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尚未進入城市群發展階段。除了一兩個地區之外,絕大部分地區談論城市群都為之過早。現階段的區域協同首先是解決國家中心城市為核心的都市圈范圍內的均衡發展問題。
第三,通過規劃、立法等嚴格管控措施,集中保留大面積的自然生態空間,實現城市與自然和諧共生。生產、生態、生活的“三生空間”,作為政治口號可以,但作為嚴格的土地利用分類,則需要回到科學本源,把理想的政治口號變成技術上可規范、可操作,可與產權制度掛鉤,與具體責任人掛鉤的科學土地利用分類上。
3. 通過社區治理,實現和諧高密度集聚
中國作為高密度生存的國家,必須提高建設強度,推進土地混合使用,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只有城市聚集到一定程度才能真正實現資源節約和生態友好,而中低密度擴展的方式將引發進一步的能源和土地資源過度消耗。
高密度地區的空間治理,難以完全通過自上而下的途徑解決。當今中國的大城市,除了空間集聚過于嚴重外,社會治理單元也高速發展。而如何建立可以有效管控的城市社區單元,通過自上而下的空間資源調控和自下而上的多元主體參與的社區治理來解決社會問題正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實現高度擁擠環境下的和諧氛圍,社區治理的作用不容小視。
四、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并不是中國特有問題。很多發達國家經歷城市化高潮后,普遍推出過國家級的鄉村振興戰略、農村振興戰略,促進農業、農村向自然和諧、生態安全、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等現代價值觀轉型。
1. 以空間屬性為核心,轉變城市與鄉村的接軌方式
我國在這一領域進行過較多探索,但從實際情況看,究竟城鄉邊界如何劃定,尚未形成成熟的方案。而錯誤或者不科學的邊界劃分將影響城鄉之間的資產分配和資產利益的二次分配。
2. 以核心價值為導向,推動城鄉差異化發展
是否要實現所謂城鄉同地同質、同區位、同權力,需要慎重研究。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現在推動的城鄉絕對同權,可能會在國家特色小鎮建設以及鄉村振興運動中帶來非理性的圈地高潮。未來農村土地價值會高于城市土地價值,在精品建造、環境友好、文化傳承方面將發揮更有效的作用。而知識階層和富裕階層,可能重新選擇鄉村定居,由此,才能真正實現鄉村振興,而歷史上有價值的鄉村遺產也正是這些人創造的。
3. 中國鄉村發展的時代特殊性
中國的鄉村振興,因為時代變革也帶來額外的挑戰——與自然保護結合,與現代化技術應用結合,與食品安全保障體系結合,以及與新一代農民培養計劃結合,而這些都涉及到根本性的農業公共體制變革問題。
美國的鄉村發展模板是與美國的自然條件、工業化進程密切相關的,強調的是規模、效益與產量,而這個模式在當今的技術條件下是否仍是唯一解?另一方面,中國極度復雜的地形地貌,也難以全盤推進美國式的大規模機械化農業。甚至在電商時代,傳統的小農經濟能否重新煥發全新的生命力,都值得關注和探討。
4. 差異化的社會公共產品供給
隨著農村空間單元功能的多樣化,大量農村地區已經不是以農業為主體,而是承載多元化的城鄉復合功能。而一直以來,鄉村地區無差別化的社會公共產品供給,勢必產生一系列問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經驗教訓很多:劇院變成家具城,文化站變成麻將館。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絕不等于簡單的設施資源均等化和設施布局均勻化。
5、 適合鄉村的社區治理模式
我國土地使用制度的二元結構和基層政權結構,導致城市規劃與鄉村規劃必然實行的兩套機制和體制,城市社區與鄉村社區的組織和自治模式也會走上完全不一樣的道路。簡單地把城市規劃改成城鄉規劃絕不意味著所有的方法論和技術支撐就得到解決了,城鄉治理模式無法照搬。因此,將國有土地管理和三農(大農業部)的管理切開就非常有異議,在此基礎上,探索一套真正適合農村基層的行政模式,適合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的規劃建設方式,是未來面臨的艱巨任務。
五、多元化舊城更新
城市既有存量土地的復興,將從簡單的物質環境的更新,走向街區社會、經濟、文化的全方位復興。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公租房制度、改善居民住房條件是首要問題,需要全新的制度設計。運用法律、規劃與財政等工具,推動城市文化和遺產保護,形成城市發展新動力,而不是一味通過“破壞性”建設以獲得發展空間。老城社會構成多元,簡單一拆了之,勢必破壞這一特征。基于社區治理,避免社會排斥,使得城市人群的構成達到均衡狀態,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的老城地區更新的重要任務。
另一方面,新城和新區在未來的發展仍會占有一席之地。新城新區發展的出發點是解決歷史錯誤,解決既有中心地區人口過度聚集、無法滿足基本居住、攤大餅發展等問題,值得進行全新探索。而從由此產生的基本土地利用模式到具體城市支撐系統的技術變革問題,給未來中國的實踐留有巨大空間。
面向未來的高質量城鎮化將體現下述核心特征:
(1)“國土均衡”:均衡不是均勻,而是各擔其職,各取所需。
(2)“城鄉融合”:這是政治目標,但不意味著城鄉完全用一個模式進行建設。一城、一鄉、一鎮、一村是有機的整體,是一個和而不同的整體。
(3)“綠色健康”:綠色城鎮化是必然道路。
(4)“智慧創新”:以科技進步為支撐,全面提升城鄉發展智能化、智慧化水平。老老實實用好現有技術,一點一點提升社會治理能力。
(5)“包容共享”:大數據時代賦予我們對目標人群深入觀察的能力,未來規劃響應多元人群的差異化需求,促進城市空間資源的公平分配及社區協同治理,建設真正意義上包容性更強的人民城市,是我們應該期待的前景。
(6)“文化繁榮”:既要對歷史懷有敬畏之心,停止對歷史資源的揮霍與破壞;更應該充分發揮創造力,為未來留下一份帶有中國特色的遺產。
(7)“治理現代”:城鄉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未來中國城鎮化可以持續健康發展的基本保障,涉及國土管理、結構優化、質量提升、整體和諧、協同治理等一系列問題。
通過發展模式和組織結構調整,建立一套全面可行的信息技術平臺,以及系統化的科學決策支撐體系,從而推動傳統單目標分治向多目標融合的治理模式轉變。邁向2035和2049,我們才剛剛起步,未來,更多新時代高質量城鎮化的具體技術策略和技術指標尚需諸位探討。
注:本文根據現場速記整理,經發言嘉賓確認